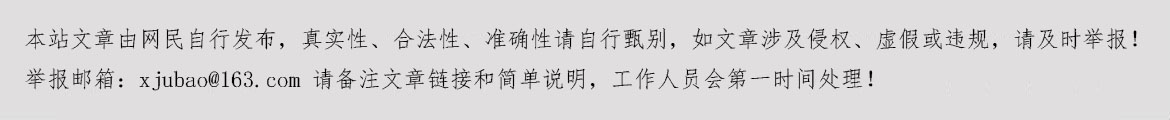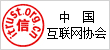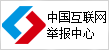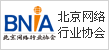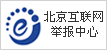黄博|赞普、国王与法王:后吐蕃王朝时代藏文史籍中君主称号的嬗变
2021-12-02 17:12:03
【本文作者】
黄博,1982年生,重庆人。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藏族史与宋史的研究,曾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全国民族研究优秀成果奖等。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出版专著有《谣言、风俗与学术:宋代巴蜀地区的政治文化考察》《10—13世纪古格王国政治史研究》等,在《世界宗教研究》《中国藏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CSSCI来源期上发表论文20余篇。
摘要
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崩溃以后,“赞普”作为最高君主称号在藏文史籍中日渐消减。13世纪前期成书的《第吴宗教源流》中记载了吐蕃王室后裔建立的众多地方割据政权,其君主仍然被称为赞普,但14世纪中后期成书的《雅隆尊者教法史》《西藏王统记》等著作则基本上以国王或国主名号指称这些割据政权的君主,到了晚期如《拉达克王统记》《安多政教史》的写作中,对吐蕃时代的赞普都不再使用“赞普”的称号,而是以“国王”或“法王”的称号替代。虽然都是早期藏族社会中的君主称号,但“赞普”拥有普通“国王”所不具有的神圣性——天神降世与权势煊赫,然而赞普的神圣性随着统一王朝的崩溃与君主制在后吐蕃王朝时代的式微而日益衰减。赞普称号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反映的是吐蕃分治割据时代新的权力结构与权力关系的来临。
关键词
赞普;国王;法王;藏文史籍
在中国古代不同的民族和政治文化传统中,存在不同的君主称号体系。中原王朝的最高君主一般采用“皇帝”之号,北方民族自5世纪后,大多自称“可汗”,而吐蕃人的君主称号则是“赞普”(btsan po)。随着吐蕃统一青藏高原,赞普也成为吐蕃王朝时代藏族政治文化传统中最高等级的君主称号。皇帝和可汗的称号自从诞生以后,就长期作为中原王朝与北方民族政权的君主称号而行用,王朝的更替和民族的兴衰,都不影响皇帝与可汗称号本身的延续。与此境遇不同,“赞普”称号却在吐蕃王朝崩溃后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目前学界对于赞普称号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较多,但对赞普称号的存续则缺乏关注。本文尝试梳理并讨论吐蕃王朝崩溃后,赞普称号从青藏高原藏族诸政权中逐渐隐去的历史过程及其原因。
一、史籍所见吐蕃王朝崩溃后青藏地区诸分治政权的君主称号
公元842年,吐蕃王朝末代赞普朗达玛·乌冬赞死后,王子沃松和云丹因争位而引发内乱,导致吐蕃王朝在青藏高原统治的崩溃。此后,王室后裔分治各地,云丹之子赤德衮年有二子,长子日巴衮一系据有山南的雅隆河谷地区,次子尼玛衮一系主要占据止贡、澎域(今西藏林周县)等地,其后裔意希坚赞占据桑耶寺一带,成为后弘期初期下路弘法的重要力量。沃松一系本来据有山南一带,但其子贝柯赞死于叛乱后,山南地区渐为云丹的后裔占据,贝柯赞二子赤扎西孜巴贝和吉德尼玛衮皆赴边地发展,前者发展出所谓“下部三德”,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开创“贡塘王朝”以及主政恰萨(墨竹工卡一带)的雅隆觉卧王系,而后者则西进象雄故地,开创阿里王系,其分支包括拉达克王系、古格王系和亚泽王系等。
后弘期藏文史籍在谈及上述这些吐蕃王室后裔政权的君主时,其名号并不统一,即便是同一部史书,给他们冠上的君主头衔也是五花八门。14世纪晚期成书的《雅隆尊者教法史》在总述吐蕃王朝崩溃后王室分治的情况时说,从此以后,“统治整个吐蕃的国王再也没有出现过”(bod spyi la dbang sgyur bavi rgyal po ni ha byung ba)。并且称末代赞普朗达玛为“国王朗达玛”(rgyal po glang dar ma)。在行文中也有“国王沃松之子国主贝柯赞”(rgyal po vod bsrung kyi sras mngav bdag dpal mgor btsan)的说法。而在叙及著名的古格国王拉喇嘛益西沃时,称未出家前的益西沃为“赞普松艾”(btsan po srong nge)。在讲述益西沃的侄孙沃德时,沃德的称号又变成了“国主沃德”(mngav bdag vod lde)。在《雅隆尊者教法史》的这段叙事中,赞普只出现了一次,为的是彰显为弘扬佛教做出巨大贡献的益西沃的与众不同;而真正的赞普朗达玛却被称为“国王”(rgyal po)。事实上,到了分治割据时期,吐蕃王室后裔建立的各个地方政权的君主大多被称为国王(rgyal po)和国主(mngav bdag),赞普之称并不多见。
跟《雅隆尊者教法史》差不多同时代的《西藏王统记》在叙述沃松与云丹时,也都称之为“国主”(mngav bdag),刘立千先生译为汉文时则音译为“安达”。该词本意为占有一块土地和人民的所有者,意即领主。其实,沃松与云丹最初为了显示各自的王室正统地位,都自称“赞普”。甚至10—11世纪前后,割据各地的沃松和云丹的众多后裔,虽然地盘越分越小,但仍然被后弘期早期的藏文史籍称为“赞普”。如13世纪前期的《第吴宗教源流》在书末专篇梳理了分治割据时期的诸王系,把沃松之子贝柯赞的嫡子吉德尼玛衮一系,即后世的古格王国诸君主,都称作“上部阿里的赞普”(stod mngav ris kyi btsan po),而割据卫藏地区的贝柯赞的庶子扎西孜巴贝一系,则被叫作“卫藏四茹的赞普”(dbus gtsang ru bzhivi btsan po)。云丹的长孙日巴衮的后裔发展出的门朗王系,被称为“雅堆的赞普门朗世系”(yar stod kyi btsan po smon lam gyi rgyud)。不过,史书中这些所谓“赞普”,后来还坚持自称赞普或者被藏族史学家们称作赞普的并不多。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汉文史料也显示,割据河湟一带的唃厮啰政权的君主仍然在使用“赞普”称号。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唃厮啰者,绪出吐蕃赞普,本名欺南凌温篯逋。篯逋犹赞普也,羌语讹为篯逋”。可见虽然汉文音译有所不同,但赞普之号其实未变。其时湟水流域的宗哥族大首领李立遵和唃厮啰争权,据《宋史》记载,“立遵乃上书求号赞普”,但宋朝意识到,“赞普,可汗号也。立遵一言得之,何以处唃斯啰邪”?宋人以“可汗”比拟“赞普”,显然明白赞普名号独一无二的地位,也可见赞普称号仍然是当时河湟吐蕃首领所追求的最高君主称号。
但是吐蕃王朝崩溃后,西藏一些分治割据政权也开始使用另外一些君主称号。“国王”“国主”是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君主称号。10世纪初期,沃松一系的吉德尼玛衮进入象雄故地,建政立国,《汉藏史集》在解释“阿里”地名的由来时说,“由于父亲吉德尼玛衮最初前来,将上部诸地纳入治下,故而后来把(上部诸地)称之为阿里”(yab skyid lde nyi ma mgon gyi sngon ma byon nas∥stod yul rnams mngav vog tu bsdus pas∥phyi ma la mngav ris zer∥)。阿里(mngav ris)即领土和属民的意思。而与阿里(领地)搭配的君主称号正是国主/领主(mngav bdag),吐蕃王朝崩溃后,赞普后裔政权的君主在藏文史籍中常被称为“国主”,象雄故地后来被称为“阿里”正与此名号有关。《弟吴宗教源流》在论述“上部阿里的赞普”时,有时就径直用国主来代替赞普,如古格王孜德就被叫作“国主孜德”(mngav bdag rtse lde)。而在一些比较后期的藏文史籍里,吉德尼玛衮的父亲贝柯赞也被叫作国主贝柯赞(mngav bdag dpal vkhor btsan)。
藏文史籍越晚出对赞普称号的使用频次就越低,而国王和国主的使用则越来越普遍,如在《阿里王统记》中,大多数的古格君主都被称作“国主”和“国王”,甚至在一句话中这两个称号还会同时出现——“古格国主拉钦孜德就是最为出类拔萃的国王”(gu gevi mngav bdag bla chen rtse lde ni ches khyad par du vphags pavi rgyal po yin)。而更晚成书的《拉达克王统记》几乎通篇都是用“国王”来描述吐蕃赞普及其后裔所形成的各个王系,无论是拉达克自己的君主,还是吐蕃王朝的赞普,都称之为国王,连在总述吐蕃王统时也说,“世代相续之悉补野国王乃吐蕃之国王”(rigs brgyud kyi rgyal po spu rgyal bod kyi rgyal po yin)。虽然拉达克的王统史仍然把吐蕃王朝的历史作为其自身历史的一部分,但赞普称号在拉达克的历史记忆中却几乎被遗忘了。
随着赞普后裔们渐渐失去了赞普之号,另一个更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藏文史籍即便在讲述吐蕃时代的历史时,也不再用赞普来指称吐蕃王朝的君主,而是以“国王”或“法王”(chos rgyal)代替。《安多政教史》的吐蕃史叙事最为典型,这部完稿于19世纪中后期的巨著在提及松赞干布时很少称其为赞普,而是冠以“法王”之号,甚至在叙述第一代吐蕃赞普时也称其为法王聂赤赞普。此外,该书在讲述著名的“噶玛洛”(ka ma log)部落来历时说,他们是吐蕃时代驻守于汉藏边界的部队的后裔,当时他们的祖先接到这样的命令——“国王(rgyal po)的命令没来之前,不得返回”。作者还总结说,“因此多麦南北等地的大多数的家族,正是从吐蕃法王(bod chos rgyal)派驻到汉藏边界的部队繁衍而来”。这段话中本该是赞普的地方分别被国王和法王替换了。
《雅隆尊者教法史》
二、赞普与吐蕃王朝时代的诸君主称号的内涵与运用
在后弘期以来的藏文史籍的叙述中,对各政权的君主称号从赞普、国主、国王的混用,再到赞普之称基本退出历史舞台,这一现象到底意味着什么?藏文史籍中赞普称号被国主和国王取代,这一历史书写习惯的形成和吐蕃王朝崩溃后西藏社会历史进程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要弄清楚这些问题,首先得把赞普的君主性质解释清楚。赞普作为青藏高原地区和藏族政治文化传统中的最高君主称号,跟皇帝、可汗一样,具有其特殊的历史文化内涵。中国古代历史上,不同的人群拥有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其最高君主的称号都是自身重要历史阶段的产物。皇帝称号成为中原王朝的最高君主称号,渊源于秦始皇对战国时代的终结;赞普成为青藏高原的最高君主称号,则是因为吐蕃王朝对青藏高原的统一。
事实上,赞普之称并非一开始就是青藏高原和藏族政治文化中的最高君主称号,最初它只是崛起于雅隆河谷的鹘提悉补野部落首领的专名。在吐蕃王朝统一青藏高原之前,青藏高原可谓邦国林立,当时各个邦国君主的通名是什么呢?敦煌写卷P.T.1286中留有一份蕃地各邦国君臣名录,这些邦国(rgyal phran)的君主都被叫作“王”(rje)。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王”(rje)并不是这些邦国君主本来的称号,因为“王”(rje)在吐蕃王朝时代的王臣位阶中,是介于赞普与贵族大臣之间的一个贵族层级,他的身份性质是吐蕃王朝的“封君”,而非真正的一国之君。“王”(rje)的出现,突显了赞普的至尊君主地位。在这份写卷的最后,有一段总论揭示出这些邦国的“王”(rje)在成为吐蕃王朝的封君之前,作为割据一方的一国之君时的真正称号应该是“国王”(rgyal po)。如象雄王被松赞干布率兵击败后而失国,在敦煌写卷P.T.1287中是这样叙述的:
此王(rgyal vdi)之时,发兵攻象雄之王(zhang zhung gI rgyal po),统其国政,象政王李迷夏失国,象雄一切部众咸归于辖下收为编氓。
这段文字把松赞干布叫作“此王”(rgyal vdi),可见吐蕃攻灭象雄前,象雄的君主是国王,吐蕃的赞普也是国王。国王就是当时青藏高原各地君主的通名。《唐蕃会盟碑》的藏文部分,对赞普的全称是“吐蕃大国王天神化身赞普”(pod kyi rgyal po chen po vphrul gyI lha btsan po),对应的汉文碑文则是“大蕃圣神赞普”。显然,赞普的君主性质就是吐蕃国王(pod kyi rgyal),赞普与国王在这个意义上是相同的,但又不等价。因为“天神化身”(vphrul gyI lha)的属性赋予了吐蕃国王以非凡的意义,赞普不是普通的国王,而是“伟大的国王”(rgyal po chen po)。
吐蕃人有一套自己的君主等级结构,陈庆英先生早前曾指出,“在吐蕃文献中尽管还有其他的对君王的称号如王(rje)、国王(rgyal po)等词,但赞普的意义与它们并不完全相同”。而白桂思(Christopher I. Beekwith)曾说,“赞普自认是四方天子中的天子,就是四方诸王中真正的王,其他王只能称rgyal po或rje,是为次等、较小的统治者,为赞普所统属”。在《唐蕃会盟碑》中,吐蕃人正是用“赞普”的同义词“伟大的国王”(rgyal po chen po)来对译唐朝的皇帝,碑文上大唐皇帝(hwang te)的藏译就是“汉地大国王”(rgyavI rgyal po chen po)。显然,在吐蕃人看来,赞普当然是国王,但国王却不一定是赞普。这一点古格统治者孜德的称号颇能说明问题,在《阿里王统记》中,他有三个称号,一是“圣王”(vphags pavi rgyal po),二是“天神降世的国王”(gnam lha bbas kyi rgyal po),三是“吐蕃的天神赞普”(bod kyi lha btsan po)。其中“天神降世的国王”这一称号的深层意识,正是“吐蕃的天神赞普”的基本内涵。
在吐蕃王朝时代,赞普具有与生俱来的“神性”,关于吐蕃王室的祖源,林冠群先生认为,“在唐代吐蕃当代就已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但站在王室的立场”,口径却是统一的,那就是吐蕃赞普是“天神或天神之子下凡,入主人间”。“天神之子入主人间”是吐蕃王朝时代对赞普起源的普遍认知,敦煌写卷P.T.1286记载吐蕃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的身世时说,他是“天神(lha)自天空降世”,“来作吐蕃六牦牛部之主宰(pod ka gyag druag gi rje)”,因此赞普是“天神之子(lha sras)做人间之王(myi yul gyi rgyal)”。吐蕃时代的碑刻铭文也经常强调赞普与生俱来的天神降世的属性,如赤德松赞墓碑铭文说“赞普神子(btsan po lha sras)鹘提悉补野,是天神下凡,来做人主”。唐蕃会盟碑也写道,“天神化身赞普鹘提悉补野”(vphrul gyi lha btsan po vo lde spu rgyal),“来做吐蕃的大王(pod kyi rgyal po chen po)”,他是“以天神降世而为人王(myivi rgyal po)”。这些措辞一方面显示出赞普的神性,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国王与赞普的差别之所在。
以上的赞普“神话”表明,赞普的神性来源于鹘提悉补野部落的政治文化传统。不过,神性并不是赞普君主性质的全部,也不是赞普最终成为青藏高原最高君主称号的真正原因,真正原因是吐蕃完成了青藏高原的统一事业,将本来只是鹘提悉补野部落首领的权势,扩展到了整个青藏高原。赞普的君主属性中除了“神性”以外,还有作为伟大领袖的属性——“圣”,因此我们可以在前引的唐蕃会盟碑中看到,吐蕃人把汉语的“圣神”合用来称颂赞普,即赞普的君主性质是“神”与“圣”的合体,这是没有神圣附加属性的国王所不能比的。
剔除神话赋予的赞普神性,在邦国林立时代,赞普的权位本来与国王是相同的,但吐蕃王朝统一青藏高原的历史改变了赞普与国王的地位和意涵。前揭敦煌写卷P.T.1286在总结吐蕃统一诸邦时说:
古昔各地邦君(rgyal phran)和大臣如此降世,成为众人之王(myi hang gi rje)和大地之主宰。国王威猛(rgyal po btsan ba),大臣贤明,谋略深沉,相互剿灭,并入治下,收为编氓。最终以鹘提悉补野(vo lde spu rgyal)之权势无敌,最为崇高。
由此记载可知,正是因为鹘提悉补野的君主最终剿灭各邦,开创了吐蕃王朝,才将赞普的权力和地位提升到了无与伦比的状态,“国王威猛”(rgyal po btsan ba)的赞辞,既是对赞普的君主身份的定位,意即赞普即国王;又是对赞普君权的升华,即赞普不是普通的国王,因为威猛的国王,才够得上赞普的殊荣。值得注意的是,“威猛”一词的核心语素就是“赞”(btsan),王尧先生认为赞本来是指苯教中一种十分狰狞可怖、凶猛暴戾的神灵,以此构词彰显的是赞普权势无敌的强大力量和令人畏服的威猛属性,可以说“赞”集合了赞普天神之子与威猛王者的双重属性。
此外,赤德松赞墓碑上镌刻的颂辞也集中展示了赞普称号的双重属性:
赞普天子鹘提悉勃野,天神化现,来主人间,教法礼仪尽善尽美,永建基业,权势煊赫,地久天长,永无颓败,社稷疆域,广袤无极,政基巩固,永垂雍仲之大业。
此处的“天子”(lha sras),准确的表述应是“天神之子”,是天神入主人间的同义语。同时赞普除了天神身份所具有的神性以外,还必须拥有世俗意义上的伟大,“权势煊赫”是对“国王威猛”的具体表述。赞普权势的具体体现还包括疆域地盘的广大,这一点恰恰和赞普从鹘提悉补野部落首领变成整个青藏高原最高统治者的历史契合。弄清了吐蕃王朝时代赞普作为君主的这两个特质——天神降世与权势煊赫,就可以理解后吐蕃王朝时代赞普称号渐渐退出藏族历史舞台的原因了。
三、后吐蕃王朝时代西藏君主制的衰落与赞普称号在藏族政治文化中的命运
吐蕃王朝崩溃以后,西藏社会陷入长期的混乱,社会秩序一度无法恢复。最终,卫藏地区政权重建的主流模式是地方贵族结合藏传佛教的教派力量,打造出一批政教合一的小型地方割据政权。于此过程中,君主制在卫藏核心区日益式微。藏文史籍普遍认为,朗达玛以后西藏的王权政治开始进入衰败期,《贤者喜宴》的偈语说:“油已耗尽灯熄灭,王权小如冬天水。王法败坏如腐绳,政权安乐如虹逝。”在经典藏文史籍中,不但末代赞普朗达玛死于非命,贝柯赞也是死于臣下叛乱,过去如天神般神圣不可侵犯的赞普一再死于非命,这严重削弱了赞普的神圣性。同时,在后弘期佛教文化成为西藏政治文化的主流之后,过去“天神入主人间”的赞普神性已经显得有些不合时适宜。石硕教授曾经揭示早期赞普王权与苯教的密切关系,指出所谓“天神”,是由苯教信仰体系支撑起来的。赞普这一称号本身就有着强烈的苯教文化意蕴,因此在后弘期的佛教高僧笔下,他们更愿意把吐蕃王朝的赞普叫作“法王”。事实上,法王的称号也有利于衰落后的赞普后裔们重获新的权威。
另外,因为统一局面被破坏,吐蕃赞普的煊赫权势也不复存在,人们不得不感慨“王者奴隶无区别,吐蕃沦为破碎境”。至高无上的赞普王权因为分崩离析而风光不再,《贤者喜宴》叙述阿底峡大师来到藏地后,“对所有一切赞普均极尊敬”。佛教大师们要求臣民们要尊敬赞普,对于赞普,不论他们是否有权势,都应该像阿底峡大师那样予以尊崇。但吐蕃王朝的崩溃,使阿底峡时代的吐蕃人感到非常困惑,他们承认赞普族系高贵神圣,过去也曾权势广大,但更感慨赞普权势如今的衰败:
那种即使帝释天王也无法比拟的权势,时至今日唯存虚名而已矣!那些诸法王(指吐蕃王朝的赞普)的大部的后裔在此后的时间里均做了属民或属民的属民;而广大的奴隶及奴隶的奴隶则高傲自大。
显然,王权的衰落不振连累了“赞普”的光辉形象,后弘期的佛教史家不得不以另外一种神圣性——赞普对佛教事业的贡献来重塑王权的价值。后世的佛教史家也都以符合佛教政治观的“法王”来称颂赞普,用佛教的无常观来解释无论赞普有没有权势都应该被尊崇,因为赞普的伟大不是来自权势,而是来自他们对佛教伟大事业的弘扬,而除此之外的一切权势都是无常的、不值得称颂。在开导吐蕃人理解这个问题时,佛教大师常说“诸世间王者们的权势,就像无常那样没有益处”,所以不必纠结赞普权势的强弱。
在藏文史籍中,后吐蕃王朝时代的历史就是赞普王权的衰落史,《汉藏史集》总结吐蕃王朝崩溃后的情形时说:“由于此等王臣福德微小,阴土牛年(869)发生造反,阴火鸡年(877)诸王陵墓被毁坏。王族变为臣民,国法毁坏,佛法衰亡,外部边哨尽失,吐蕃内部大乱。”随着内外局面的持续恶化,赞普王权对吐蕃王室的专属性似乎也不复存在。在《朗氏世系灵墀宝卷》中,朗氏家族祖先绛曲哲桂(968—1076)在给子孙的教诫里说“谁拥有地盘,他就是那个地方的主人;部落首领大公无私,就是地方上的主人”,甚至宣称“勇士成为主人就是赞普”(dpav bo sa bdag vdzin pa btsan po yin),强调“谁善于守住地盘,谁就有赞普的世系(yul vdzin shes na btsan povi rgyud)”。这些话说得如此直白,简直是中原乱世时代所谓“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的西藏版了。
吐蕃王朝的成功把以赞普为称号的君主制推向了顶峰,但吐蕃王朝的崩溃也把王权政治带入了困境。赞普后裔们无法重新整合西藏社会,王室内部还不断分化,此后君主制只能在藏族社会苟延残喘。以贝柯赞一系为例,该系在贝柯赞死后无法在卫藏地区立足,不得不远走边地。吉德尼玛衮在阿里立国,但他死后分化出所谓“上部三衮”;赤扎西孜巴贝去了拉堆,后来分化出所谓的“下部三德”。我们可以用《贤者喜宴》所载下部三德的情况为例,来体会一下王室的这种不断分化与分治的特点。书中叙述长子贝德一系占据贡塘等地,发展出贡塘王系;幼子吉德的子孙去了北方,成为“叶如及如拉之赞普”;次子约德有四子,分布在藏容、努域和娘堆等地,其中约德次子赤德去了多康,三子尼雅德之后裔即叶如之吉卡赞普,四子赤琼前往雅隆。其后又分出所谓的“臧擦六兄弟”,分治昌珠、青、恰、雅达、邦孜等地,皆各据一方,互不统属。王室的不断分化与分治彻底摧毁了吐蕃时代赞普无人可比的煊赫权势,更无法恢复昔日赞普时代带给人们的稳定和繁荣。
君主制整体式微,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佛教势力主导的政教合一体制的蒸蒸日上。这一时期,地方贵族一方面利用自己的财力积累佛学知识,为自己赢得社会声誉,如昆氏家族的官却杰布(1034—1102),“将家中的一部分土地卖掉,奉献十七匹马以及珠串珍宝”,向卓弥益师“请求授予佛教语诀。上师授予了一部分修道次第等佛法,尤其是授予了三密乘部之广说。他成为执持教法的五大弟子之首”。地方贵族以高僧的身份填补了赞普王权衰落留下的社会权力真空,而成为了地方社会的新权威。“赡部之权独大揽,神采奕奕放光华”,这句出自《萨迦世系史》对官却杰布等人的赞词,正说明了佛教文化所塑造的新权威将会成为后吐蕃王朝时代西藏社会新的权力来源。在当时的西藏社会,君主的地位已渐渐不如高僧,成为佛教高僧逐渐成为后吐蕃时代最崇高的人生理想,如噶举派的祖师岗波巴(1079—1153)早年在家乡时曾听到三个乞丐的发愿,一个认为能够吃上一坨糌粑团和一碗佐食菜就是很快乐幸福的事情了,另一个则发愿想要成为古格国王孜德那样的君主(smon ne na mngav bdag rtse lde lta bu la smon mod),最后一个则希望像米拉日巴尊者那样对衣食没有贪恋、可以在虚空中飞来飞去。而岗波巴选择了最后那个人的心愿为自己的人生目标。
另一方面,地方贵族还将自己的财力投入到寺院建设中,形成以本派教法为核心,以本派寺院为基地的区域型政教合一的准政权组织。1073年昆氏家族的官却杰布修建了萨迦寺,当时他“请求该地之主人觉卧顿那巴售之,获得同意。又对该处之领主象雄古热瓦、四个僧人村庄和七个俗民村庄等人”宣布要购买这块土地来修建寺院,最后“以一匹白骡马、珍珠鬘、一套女装而购得该地,自门卓以下,派卓以上皆归嘛喇(官却杰布)所有”。显然,无论是学得佛法,还是修建寺院,昆氏家族的财力支持是他坚强的后盾,同时这笔土地交易颇有些半买半送的性质,当地的地方首领因为官却杰布佛教高僧的新权威身份,为他修建萨迦寺而购置土地的“生意”大开了方便之门。
萨迦寺既是萨迦派教法创造和传承的文化中心,也是地方行政管理机构,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1182—1251)主持萨迦寺时,他的弟弟索南坚赞(1184—1239)实际上负责了很多地方行政事务,“从辛莫且开始修建了一箭之地等长的围墙,在斯塘等地设立了集市和人口众多的村庄,在仲堆、仲麦、达托、芒喀寨钦等地建立庄园,在绛迥、喀索、果斋、客尔普等地建立了许多牧场,在热萨等地牧养马群”。所以萨迦派的教团组织,实际上就是一个以教派为核心的区域性准政权组织,跟君主制政权比起来,其优势在于大大强化了内部的凝聚力和周边地区的向心力,《萨迦世系史》总结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的事业时说:
法王萨班有大、中、小三种寺院。大寺有具吉祥萨迦寺和北方凉州寨喀寺;中等寺院有桑耶寺、年堆江图尔寺、香色新寺,小寺遍及康、藏、卫等各地。此诸寺俱由法王萨班管辖,总计有显密教法,尤为注疏等法相之说是法王萨班之独特的优良传统。
昆氏家族的这种新模式在君主制衰落后为西藏社会走出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一模式不但克服了吐蕃王朝崩溃后君主制政权日益碎片化的困境,而且还能不断地聚沙成塔,越做越大。《萨迦世系史》在颂偈中把昆氏家族的宗教领袖比喻为兼具“佛法僧三宝”的“执政王”(sa skyong rgyal po),反映出这一模式在赞普王权之外开创出一种新的王权模式。特别是萨班·贡噶坚赞被冠以“法王”的称号,而法王有着安定社会秩序的强大功能:
法王无论居于何地,此地即不会出现鬼魅制造的瘟疫,内外战乱和天灾人祸;法王行于路途,路途抢夺他人财物之事即会消失,所有行路之众生亦将互敬互爱。总之,法王在某处住多久,当地在此期间就根本不会出现外战内乱。
显然,伴随新王权模式的开创,法王基本上已经取代了赞普的权威,在神圣性和权势上都盖过了那些僻居一隅的赞普后裔们。不过要注意的是,贡噶坚赞的法王称号——“chos rje”,其字面意思是“法主”,说明其身份只是宗教首领;这不同于稍后出现的另一种加在八思巴身上的法王称号——“chos rgyal”,该称号通常是藏族史家对吐蕃时代那些对政教事业有巨大贡献的赞普的敬称。《萨迦世系史》称八思巴是“住世的菩萨,发愿教化南瞻部洲之大部”,因此“转生为桑擦之子,治理卫、藏、康三处吐蕃地面之大部”。八思巴不仅仅是宗教首领,更是以佛法治世的政治领袖,萨迦法王的称号从“chos rje”到“chos rgyal”的变化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因此在元朝扶持萨迦派主理西藏政务之后,萨迦政权的政教首领已经有如“吐蕃国王”了,帕竹政权的开创者绛曲坚赞曾说:“萨迦大寺的上师住锡细脱拉章,他与知事僧众一起肩负权责,就像吐蕃的国王一样(gdan sa chen povi bla ma gzhi thog tu bzhugs pa de dang∥zhal ngo mnyam par kun gyis vkhur dgos shing∥pod kyi rgyal po lta bur yod vdug pa)。”当然,“像”国王,也就意味着不是“真”的国王,吐蕃王朝崩溃后,君主制一蹶不振,西藏的主要政治势力大多由宗教力量把持,各教派政权只有事实上的政府首脑,而没有名正言顺的最高统治者,西藏各势力只能在君主制之外寻找新的领导体制,这就造成了君主制在吐蕃最辉煌的成果和象征——赞普称号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贤者喜宴》
四、结语
后吐蕃王朝时代,政治上的分治割据局面长期存续,像吐蕃王朝那样的统一政权再也无法建立起来了。到13世纪初,恢复统一的吐蕃王朝的可能性已经在长达四百年分治割据中被消磨殆尽。在后弘期的佛教史叙事中,吐蕃的赞普渐渐被各个王系的国王所代替。但值得注意的是,国王并不是吐蕃王朝崩溃后为因应分治割据现状而新创的称号,国王实际上也是吐蕃王朝时代既存的政治符号,只是其权力地位和象征性价值都低于赞普而已,其本身就体现着不同时代藏族文化的政治传统。赞普称号的退场,标志着吐蕃分治割据时代新的权力结构与权力关系的来临。
此外,这个时期的藏族社会,虽然在政治上四分五裂,但在文化上却并没有与吐蕃王朝的历史割裂,割据各地的王系在书写自己的历史时都坚持接续吐蕃王朝的历史,并把吐蕃王朝的历史当作自己的历史的一部分。但后弘期以来新形成的历史书写传统又改造了人们对吐蕃王朝最高统治者的历史记忆,极力塑造着一个全新的吐蕃赞普神圣系谱,把赞普变成法王,潜移默化地重塑了吐蕃王权的神圣性。王统史与教法史双管齐下,一定程度上既改造了人们的历史记忆,又保留了吐蕃盛世的美好回忆。无论是赞普式的法王,还是法王式的赞普,都反映了藏民对太平时代的向往。最后,在后弘期藏族史家的笔下,吐蕃王朝的最高统治者还是赞普,可是这个被赋予了法王属性的赞普已经不是原来的赞普了。
编辑:秋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