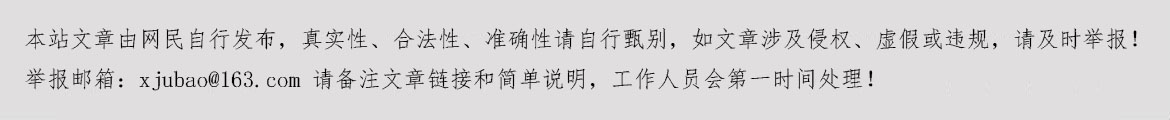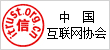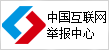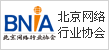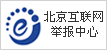绝命越野:他们为何不肯回头?
2022-01-18 18:55:42
172人参赛,21人遇难。甘肃这次百公里越野赛可以说是马拉松越野赛历史上最惨重的一次灾难,何况中国的顶尖选手在此次事件中几乎团灭。
为什么高手殒命更多?互联网上热烈讨论的失温又是怎么回事?这类活动应该如何组织?户外风险又该如何防控?我们又该如何理性看待户外活动?
大河孙: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绝命马拉松。5月22日,在甘肃举行的山地马拉松发生了一起重大灾难。172人参加百公里山地马拉松,结果21人遇难。这是户外活动和山地马拉松历史上最惨重的一次悲剧。并且,好多牺牲的选手都是国内顶尖选手,比如31岁的梁晶,他是中国好多纪录的保持者,结果这次也遇难了。
这里有很多问题需要答案,例如,遭遇这种极端天气,为何比赛没有及时终止?赛事组织到底有哪些漏洞?选手自身在碰到类似意外情况时应该怎么办?
方玄昌:这个事件无疑是一场灾难,很值得我们去认真分析。在此我想大致解答一个读者关心的问题:为什么这次比赛中那些罹难的更多都是最优秀的选手?成绩前6名的选手只活下来一个,叫张小涛,他实际上也是九死一生,在昏迷2小时33分钟后被当地牧羊人救出,侥幸逃过一劫。
我想,有3个原因可以解答这个问题。
第一个原因是这些最优秀的选手跑得最快,一出发就冲在最前面,早早进入了无人区,等到天气发生巨大变化之后,他们更不容易回头,并且获得外来援助的可能性也变小了。
第二个原因,是他们的争胜意识更强,更不愿意中途退出。当天有几个理性选手中途主动退出,他们争胜的欲望可能就没有那些最优秀的选手强。
还有第三个原因,这些成绩越好的选手,体型往往越瘦。体型越瘦的人在低温环境下,相对更容易出问题,更容易失温。
这三方面原因导致成绩最好的选手率先遇难。这真的很让我们痛惜,我相信凡是有过户外经验的人,对此都会感同身受。
选手在抱团取暖。图片:网络
花云:我要澄清一下,本次比赛是山地越野赛,超长的100公里,它和我们平时所理解的马拉松有本质区别,所需要的准备和训练都有很大差别。
我阅读了赛事规程,它设置的一道门槛是,只要你参加过马拉松,或者参加过50公里以上的越野赛,就可以参加。这个门槛设置得非常低,导致媒体的报道和个人参赛者的认知都有偏差。大家都低估了这个线路的风险和难度。
造成这次重大事故的原因是综合性的,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才发生的。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装备。都说艺高人胆大,很多时候高手的装备都会追求轻量化。
大河孙:有人就不是这样。罗静是一个登山选手,也参加了这次赛事,她因为有登山的经验,一定是按照最保守的考虑,按照当地恶劣天气的风险来准备自己的装备,这是她此次安全撤离的重要因素。
方玄昌:罗静在山地马拉松领域不是高手,她争胜欲望没有过强,反而避免了冒险的问题。其实选手们的装备趋于激进,把很多必要的装备舍弃,也是争胜欲望过强的一个结果。
花云:参加过山地越野马拉松赛事的人,都应知道所谓的强制装备。但偏偏就是这次活动,把很多必要装备列为建议装备了,而不是强制装备,比如冲锋衣。这给选手们释放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就认为这些装备可有可无。
另一个突出原因是赛事组织方提前一天就把运动员的一些装备放到了第六赛段,也就是说60公里以外了。但是我们做风险评估时,是一个实时的、动态的过程。如果赛事组织方没有提前一天把运动员的应急装备拿走,那么第二天起来,运动员感受到天气变化,可能会临时增加装备。这个时候发现没应急装备了,很多人就会抱个侥幸心理,那就继续走吧。
整条线路我看了一下,最难的就是第二赛段到第三赛段这一段线路,爬升多。对于优秀的越野选手来说,10公里只是热身,他刚热身完,此时你让他选择退赛,我觉得不太现实,这可能和他的激进没多大关系,他觉得我的身体才热起来了,准备开始发挥了,刚好要进入一个拉开成绩的时机,怎么可能马上退出?如此,第一集团的高手就快速前进,一旦问题出现,他们下撤的可能性和被营救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
方玄昌:张小涛被牧羊人发现并救下来前,他已经昏迷了两个多小时,这事实上已经是个奇迹了。失温是很可怕的。
花云:失温,就是说人体产生热量的速度明显低于热量散发的速度。牧羊人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我们在去高海拔徒步或者去雪山攀登时,风险管理中一定会请当地向导,为什么?因为如果没有当地向导,大家都不熟悉当地的山地环境,在出现问题时,就没办法找到一个好的环境来解决问题。如果是外地的向导,即使他熟悉线路,他也不熟悉线路周围的环境。
我看到一篇报道说,一个当地的牧羊人救了6个人。其实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警示。为什么牧羊人能够救出6个人,然后还把他们带到一个窑洞?就是因为他对当地资源充分了解。所以我觉得当地向导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那些打卡点的志愿者,甚至都可能不知道哪里有窑洞能够避风救人。
包括志愿者的数量和专业能力,是否能够达到应急的状态,他们是否能够及时帮助这些面临风险的选手,都是问题。
大河孙:提到失温,在那种大风或者湿冷的环境里,这些选手的体温可能会快速下降。可能有人以为体温降几度,好像没问题。实际上是很危险的,失温状态意味着一个人已经到了生命的边缘了,人可能会进入一种冬眠的状态,就是昏迷,接下来能不能恢复,还得看救援措施。
方玄昌:失温过程跟热射病是相反的,热射病是体温上升,人体控制温度上升的机制丧失了。
在户外,失温死掉的人远远超过热射病。
花云:那么失温之后,我们该怎么办?首先肯定是阻止热量流失,要去根据导致热量流失的原因,针对传导、辐射和蒸发等因素处理。
比如说辐射,增加衣服就好。在活动前做准备时,针对不同环境,携带的物资里面就要有羽绒服等防寒衣物;针对对流,我们就需要紧急找一个避风的地方,隔离大风;针对传导,一个人失温后,我们不能让他坐在冷石板等冰冷的物体上,要用保温毯等将他跟冷源隔绝开来,防止热传导;针对蒸发,我们遇到湿冷的环境,需要及时把湿衣服换掉,换上干衣服。
方玄昌:一般来说,在户外如果遭遇这种事,大家手足无措,常常都是因为准备工作做得不足,导致想要隔热,结果发现羽绒服没带或者是湿透了等等。其实即使是这样,我们常常也能够找到一些平时不是用来预防寒冷的物资,可以紧急使用。常常跟我一起爬山的人可能会注意到,我背的一直是一种简陋的塑料泡沫防潮垫,它其实比那种充气的防潮垫要好。我为什么这么认为?因为在必要的时候,它可以成为我们用来隔热的器具,这种塑料泡沫防潮垫裹在身上可以起到保温作用。
如果你身体湿透,并且所带的衣服也全部都已经湿透,这个时候也还有一种方法防寒,你可以找到一些山崖底下的干草,把干草塞到自己的衣服里面去,把衣服裤子全部塞满,这样即使外面的衣服还是湿的,它也可以帮你保温。
作为一个资深的户外爱好者,至少要有这个意识,危急时要看看周围还有没有并非你自己带来的东西可以用来保温。平时我们就要有这种动脑子的习惯,慢慢就能养成到处都能寻找救命稻草的意识。
图片:CFP
花云:方老师说的这点更多的是一种个人经验,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要靠预防,主要还是在人的因素,所以我们在去做风险评估的时候,我们首先会考虑环境的因素,有的环境你是找不到这种好的介质去保暖的。这个时候出行前就要准备足够多的装备,或者说针对性的装备给自己提供好的防护。
方玄昌:而且需要多重防护。举个简单的案例,2019年7月7日,我带队去小五台,我们7个人在北三垭口曾经遭遇过很危险的一次事件,我们7个人遭遇了雷击,每个人都被电得发麻,雷击之后是无边的寒冷,当时大雨倾盆,所有人都浇透了,气温降得非常低,逼近0度。
应对这种情况,我刚才说的多重防护,首先是我们登山包外罩一定要罩好;这还不够,有的时候雨水会横向过来,你罩好了防雨罩,背包里面还可能湿透。所以还需要第二重防护,我出发前就用塑料袋把用来防寒的衣物包好了。
花云:考虑到天气的动态变化,行前打包的时候就一定要做好防水处理,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步骤。
方玄昌:户外有一些地方,看天气预报意义不大,比如我刚才提到的小五台,还有大家更熟悉的鳌太线,太白山、鳌山那边,无论天气预报多么晴朗,你都要做好它会下雨的准备,因为它的区域小气候变化太快了。这些地方,几分钟之前晴空万里无云,几分钟之后可能马上就大雨倾盆,这种情况在我看来是常态。
花云:刚才方老师提到天气预报不准确的问题,其实很多年前我们国内就有这种购买局部区域气象预报的服务。比如说登珠峰,就要提前和相关部门采购这种局部区域的气象预报。
方玄昌:刚才说的行前准备就要考虑到各种因素,其实还包括一条,就是出行之后如果出现了一些明显的意外,作为领队和队员都应该做好回撤的准备。这一次甘肃事件发生后,我看到已经有人在指责组织方没有及时终止比赛。
我昨天带队走三峰,那也是一条国际山地马拉松比赛线路,下山的时候已经在讨论这个事,有队员问我,如果你参加这个活动,会在哪个阶段退出?我看到报道,这项赛事的赛道是出发之后有一段长下坡,长下坡结束之后,风越来越大,大家热身热不起来,我认为这个时候就应该考虑要退赛了。到第二赛段,进入10~20公里这个样子,说是有一个900米的爬升,当时已经下起倾盆大雨,这样的情况下我肯定是要退赛的。
我这样说,可能很多人会认为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但实际上,类似的事我身上是发生过的。2008年7月7日,大夏天进小五台北沟,那次不是我带队,是我的另外一个老同事黎立带队,他是绿野的杰出领队。当时我们一共26个人,原来我们的计划是走北东线,一天走完;进北沟之后雨越下越大,到北一垭口,我就建议大家尽可能原地休息之后就下撤,因为气温已经降得太低了。那一次26个人只有我和黎立两个人登顶,登顶北台就回撤了。下撤过程中看到很多人已经非常狼狈,路太滑,我们平时走3个小时的线路,那天可能需要5个甚至10个小时,很多人几乎下不来了。当时我还从树上“摘”下来一个人——她在草坡上滑出去,飞到树上,夹在了树枝丫间,上不去下不来,还是我爬到树上去把她提下来。
在户外,各种各样的情况都会发生。你如果在一定的阶段还可以回头,不回头就有可能酿成巨祸、出现惨剧。
花云:我之前是参加过这样的赛事的。也来说说关于回撤的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条线路是什么样的。其出发点是一个长下坡线路,而且是在景区石林里面穿行,由于地形的阻挡,这样的小环境可能对外部的大风感觉不明显,并且是在景区里面,人的安全感会强一些。出发长下坡是很好的热身赛道,而从第一赛段到第三赛段是一个高强度的爬升,这个阶段是拉开距离的一个阶段。这时天气变化了,但这时运动员心里会想,可能扛一扛就过去了。
对于百公里来说,前20公里其实就是一个热身;如果组织方没有强制性地宣布停赛,那个阶段你要让一个专业选手去选择退赛,我觉得可能性还是太小。
当天的比赛现场。图片来源:黄河石林大景区微博
方玄昌: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组织方的责任还是挺大的。不过我估计在这次事件之后,将来类似的比赛可能很多人的心态会发生变化。昨天浙江莫干山那边有一场山地越野赛,据说有100多个人在听到甘肃这个事件之后,中途就退赛了。昨天浙江那边气温也比较低,城区大概是在20度左右,那么在山里面应该是在15度左右,这个温度暴雨之后,你如果始终处于运动中,一般来说还不至于失温,但也会有一点点风险,但这个风险,我相信如果没有甘肃这个事件,大家都会扛过去的。
大河孙:组织方确实需要担当,业内可能都知道的,2020年的北京国际越野跑挑战赛,原计划是5月4日到5日举办,那个时候疫情还比较紧张,组织方就说因为疫情的原因,加上当时的天气原因,这个比赛就取消了。可能北京还是比较保守。
方玄昌:这个不能算是保守,我认为这是正常的、正确的做法。
刚才我们说到,户外失温是很大的一个风险因素,中暑是另外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北京这边考虑得很多的,是雷击,恰恰这三种情况,我在户外都遇到过。雷击可能相对比较少,但北京举办比赛的三峰线路,恰恰阳台山和妙峰山都是雷区。
我在小五台遭遇过两次雷击,一次是在南台,一次是在北台。北台上面有个铁架子,它能起到引雷作用,它跟避雷针不是一回事。避雷针是通过尖端放电,把大气中的电荷给它释放掉;而引雷不是利用尖端放电,而是通过金属对电的引导,把一个本来可能不在这里释放的雷电,当云层经过这个地方时让它在这里释放掉。
2019年那次,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北三垭口,铁架子离我们只有直线距离300米左右,当时风险是比较高的,我们旁边一支队伍有帐篷的金属杆都烧融了。我们当时受到的威胁主要来自于跨步电压。雷电释放点周围一定距离之内都会有较高的跨步电压,我们当时坐在湿透的帐篷里面,相对来说跨步电压不大,所以当时只是身体被电麻了,还不至于出人命。
我在南台那一次看起来危险可能更大一些,当时我们扎营的时候完全是大晴天,扎在南台巨石阵的旁边,结果到半夜的时候风云突变,大概有一个小时左右,雷电就一直在我们眼前,几十米到一两百米距离,不停放电,场面很恐怖。我当时是新闻周刊科学主编,科学这一块大家都听我的,我让大家千万不要出去、不要惊慌乱跑,帐篷里面保持干燥,外面的雷击就不会影响到我们。一个小时之后,天空重新放晴,万里无云满天繁星。
花云:我们风险管理的一个核心就是考虑变化。风险肯定不是一成不变的,当环境发生改变的时候,我们所考虑的方向也要去改变。但我一再强调的是人的因素,包括我们的身体状况、经验技术,以及心理承受能力、沟通交流的能力和方式,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
方玄昌:从人的因素看,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户外爱好者的自我认知。
拿我自己来说,我在户外常常会背很多水。我们刚才谈到雷击、中暑、失温这些风险,其实在户外还有一种风险因素是水,我始终把它看得很重,因为我知道在户外有很多人死掉是由于脱水导致的。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让自己身边保留比我走完全程还要更多一些的水。我对自身的认知,就是我的体能没什么问题,但需水量大。
还有一点,有一些人会觉得我有点多虑,我在户外的时候常常会较多地考虑别的队员、甚至其他队伍的一些状况。在我从事户外活动的这些年里,有一种情况已经出现过很多次,我自己带的队没事,但跟我们同行的其他队出了问题。
由此我在做物资储备的时候,常常有一些冗余。比如我一个人出行,也会背上三人帐,它有9斤重。这是由于若干年前有过一次事件,也是在小五台上,另外一支队伍的4个队员把主要的装备都雇当地的一个背夫给背走了,结果背夫走得快,把他们甩开了,结果他们就跟着我们这支队伍走。当天晚上我们在北二垭口扎营,他们帐篷、睡袋、防潮垫什么都没有,吃的东西也没有。当时我们的帐篷已经满员,我说服隔壁另外一支队伍腾出了一顶富余的帐篷,给这4个人挤住。
4个人挤一顶帐篷可能会把帐篷挤坏,但我认为是有必要的,否则当天晚上可能就有4具尸体需要我们搬下去,因为晚上下起雨来之后,气温降得非常低。我当时把我带的食物和水,分了一半给他们,导致我们下山的时候,我们这支队伍食物不够了。从那以后,我每次背的东西,尤其是水,总是下山的时候还会剩很多,而且我要让我的队员都多背水,他们常常不理解,但其实慢慢会理解。
大河孙:这是你们长时间做领队做出来的一种经验或者是教训吧。
方玄昌:十几年前还有一次,也是在小五台,我在北二垭口往北三垭口的路上遇到一个彪形大汉,身高大概在一米九左右,他从东台那边往这边走,看到我的时候整个人都蔫下来了。然后他有气无力地问我:哥们有水卖吗?要给我1000块钱一瓶。我一看他那样子,马上给了他一小瓶,我说你先喝掉,他一口就喝完了;我让他坐一会,再给了他一瓶,他又一口就喝掉了;又等了大概5~10分钟,我再给了他1瓶,他一口又喝掉了。3瓶水喝完之后,我又给了他4瓶水,让他留在路上慢慢喝。
他当时那个样子已经脱水非常严重,我估计他身体至少缺水3升以上。我当时带的水很多,大概有20多升。如果我不带那么多水的话,我就不敢一下子给了他好几升水——绝大多数人上山所带的全部的水也不一定够这个哥们一个人喝。
花云:我们在户外去评估人的风险的时候,还有一个维度,就是要考虑其他的户外爱好者。我记得前年就有一个户外的事故报告,一个登山者在高海拔雪山攀登的过程中,和其他队伍产生冲突,双方用冰镐打架,不仅头破血流,更严重的是他身上的羽绒服被划破了。还好,后来没有出人命,这在高海拔区域绝对是万幸。
由此我们反思,户外不仅要评估我们自身,是不是还要去考虑到同环境下其他的户外参与者可能给我们带来的风险?
方玄昌:依然可以通过故事来说明问题。我的一个朋友叫风石长安,他带了29人的一支队伍上太白山,扎完营之后去登顶,回来发现自己的帐篷、睡袋、防潮垫全部被破坏掉了,另有一支7人的队伍过来偷盗,把品牌帐篷、睡袋、防潮垫全部拿走,把比较便宜的装备全部给破坏掉。
风石长安知道这是灭顶之灾,他们面临着全军覆没、全部冻死的威胁。他当机立断,连夜带着29个人下山,下山的过程中追上了那支队伍,把这7个人全部抓起来,送公安局之后,派出所不作处理,认为这不是事。
当时我在微博上谴责过,认为这是谋财害命的行为。当时很多网友认为我说这话过激了,我相信前天甘肃这个事发生之后,大家应该都清楚,这就是谋财害命的行为。风石长安他们遭遇的事件导致了后来太白山被封闭,不让旅游攀登了。
一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这是人类户外史上最恶劣的一次事件,也是政府管理部门处理最不得当的一次。那次如果不是领队果决,有可能29人全部遇难;即便他们连夜下山,在黑咕隆咚中穿行石海,风险也是极高的,过程中摔死几个人是很正常的。风石长安凭借丰富的户外经验,才把这29人全部安然无恙带下山,我认为是个偶然结果,必然的结果应该是会出人命的。
这类“人”的因素,我们恐怕很难预先考虑到。但作为一个领队,遭遇这种情况就得当机立断,我认为当时风石长安的行为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标杆。
5月23日,救援人员在事发区域展开搜救。图片:新华社
大河孙:我们今天聊天有几个点,一是要尊重专业的知识和经验;另外一方面就是人的因素,户外的生活有很多不确定,需要依靠团队的互相支持,甚至跟其他团队的互相支持。日常在城市生活里,看到一个老人倒地了,我会考虑是不是帮他会遭遇碰瓷?这种心理在户外是不能有的。
另外一点,决定很重要。如果领队做不好,这个决定很可能要导致全军覆没,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
方玄昌:我想最后还是要跟广大的户外爱好者说一声,即使甘肃这一次出了如此大的灾难性事件,也不要因此而放弃户外,因为户外能给我们带来无穷的乐趣。风险我们总是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规避,或者是把它减到最小。既不能因为甘肃这个事件而放弃户外,也不能因为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件而不注重户外的风险管理。管理者也不应该再像当年陕西一样,由于一帮人偷了装备差一点导致29个人死亡,就把山给封掉了。我不期望这次甘肃事件导致世界范围内,尤其中国范围内这种百公里越野赛彻底给灭掉,我们需要的是科学管理。
花云:其实风险是可以适当保留的,在安全可控的范围内,做一个适当的风险保留有其价值所在,能够让我们更好去成长,从中学到更多的东西。
大河孙:不管怎么说,户外生活现在已经越来越主流化了,在户外可能会得到不一样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它能帮我们更好地认识自我,认识自然,所以我们还是要往前走。
方玄昌:当年乔治·马洛里在回答纽约时报记者提问的时候,说的那句非常有名的话,为什么要登山?因为山在那里。这属于虚无缥缈的回答,只有登山的人能体会。但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对于为什么要去探险,为什么要去参加户外?其实我们可以回答得更实在一些,那就是户外能给我们带来无穷的乐趣。你参加户外和不参加户外,生命状态是不一样的,你体会过一次就会发现,原来到外面来,我的天地会更广阔,这种体会非常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