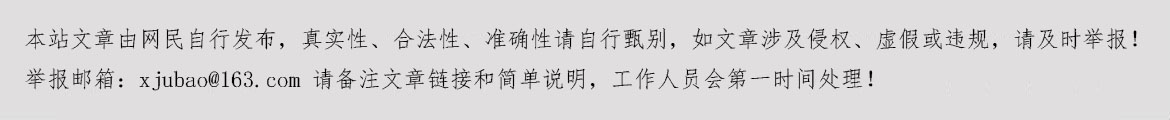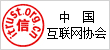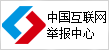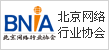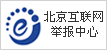张医生,人间不值得!
2022-04-12 10:51:14
“考砸锅的冒牌大神,被过去的脑残粉拉下神坛!”
近期,张文宏医生微博下面的留言,各种“口吐芬芳”,一片惨不忍睹。
随着上海疫情的爆发,和封小区甚至封城等举措,张文宏医生成了这场灾难的替罪羊。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初,张文宏的发言,得到了国内大众的追捧。
但转眼之间,张医生就成了“千夫所指”……
他在前不久所说的“新冠毒力明显降低了”、“在英国,致死性低于流感”等,被一些人上纲上线到“不爱国”、“汉奸”的程度,各种诛心之论不绝于耳。
——这究竟是怎样的人间?!
“一时把你捧到天上,一时把你踩入泥塘:这就是公众,其翻云覆雨的变幻,和‘群情激愤’背后的残忍、反智,与暴君无异。”
这番话,出自当代社会心理学家赛奇·莫斯科维奇的《群氓的时代》一书。
这本书,确实值得读。
识字的文盲,情绪的奴隶
“当代的舆论场上,每个人都识字,其中不少人甚至有着良好的学历,但汇聚在一起,就难免成为看不懂‘人话’、讲不通道理的‘文盲’。”
“而且极端的偏执、可怕的敏感、近乎荒唐的自大,和极度的不负责任……他们的言行,完全受一时的情绪所支配,不讲道理、没有逻辑,可说是‘情绪的奴隶’。”
这是赛奇在书中,对当代公众的描述,他将这样的公众称为“群氓”。
此书在西方,也曾引发很大争议。
有些人认为赛奇对公众过分贬低,不无偏见。
但同时,却也普遍承认,其思想和观点,深刻、尖锐,尤其是一针见血地针砭时弊。
张文宏医生在这两年的“过山车”——从成为网红、被誉为“百姓最喜爱的医学专家”,到突然遭受网暴,甚至被喊打喊杀——就堪称书中观点的一个典型注脚。
两年前,疫情爆发之初,身为传染病顶级专家的张文宏,临危受命,担任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
“让党员先上”、“不能让老实人吃亏”、“企业老板给我们捐东西,让员工在家里办公,隔离观察,还给人家发工资,这就是对国家做贡献了。”……
他也为医护人员和防疫志愿者的权益呼喊:
“避免无谓的牺牲,如果没有防护你可以拒绝上岗,医生要有免于受伤害的权利!”
这些大实话,接地气、有人情味儿,这在国内,成为一股难得的清流。
这样张医生受到众多网民的喝彩、关注。
同时,他过去常年行医的点点滴滴,也被不少患者记起,发在网上。
医术精湛、不收红包、对病人细致入微的照顾:
比如对听力不好的老年患者,在处方纸上,一笔一画地写“医嘱”,包括去哪里缴费、取药,和“拿到报告后在几层几号房间找我复查,不要再挂号”……
多年来,张医生都不知道救治过多少人。
新冠爆发,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压力山大。
按照国外的数学模型,拥有数千万人口的上海,很可能会有近百万人感染,最好的情况,病例也会破万。
须知,在病毒变异和疫苗普及之前,新冠的死亡率,至少2%,在一些地区近10%。
但时至今日,上海因新冠去世者,只有7人,全部发生在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出现之前。而那时上海,两年来的患者总计,也不过数百人。
与此同时,张文宏一再强调,防疫的同时,也要确保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不受影响,“就像瓷器店里抓老鼠,老鼠要逮住,但也不能砸坏了瓷器”。
这不仅是公开的承诺,也是上海在疫情期间,长期一枝独秀的事实。
这样的成绩,堪称世界级的奇迹。
坐镇上海指挥防疫的张文宏,显然功不可没。
张医生从不希望自己被热捧,只期待疫情过后,继续做个平凡的医生。
然而,今年三月中旬,疫情在上海“大爆发”——绝大部分都是无症状者,重症比例极低,新增死者至今为零。
从奥密克戎毒株“高传染,低毒力”的特点看,这种情况在全球任何一个大城市,都可能发生,哪里都难免。同时,是否依然要坚持两年前的“清零”,也值得商榷。
张文宏在过去两年,居功至伟,在这一波疫情中,至少,也并无明显过错。
他公开谈到“奥密克戎的致死率低于流感”,也是建立在充分的事实之上,
——可惜的是,很多网民不讲道理,更不肯思考、分析,只有无节制的情绪的发泄。
无论之前近乎肉麻的热捧,还是现在的指责和谩骂,乃至喊打喊杀的罗织与举报,都是“情绪上头”的产物。
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更无法叫醒那些恣意发泄、陷入疯狂的“群氓”!
劣币驱逐良币
书中也讲到,“不讲道理,只有情绪发泄”的公共舆论环境,所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劣币驱逐良币”。
“劣币驱逐良币”,最初是一个经济学现象,由英国经济学家格雷欣最先指出。
在金银铸币时代,那些成色不足的金银,会被优先花出去,成色好的则被攒起来。
于是,市面上的货币,成色越发低劣,成色好的则被“驱逐”出市场,退出流通。
而在公共舆论场上,也经常出现与之类似的情况。
既然说真话的下场是,是遭受“群起而攻之”,或者今天把你捧上天,明天让你摔得更狠,那么,明哲保身、三缄其口,就成了最理性的选择。
或者,索性只说大家爱听的话,无论真实与否。
如今,张文宏“闭嘴”了——对自己微博下面的各种指责、嘲讽和谩骂,一句也不辩解,甚至没有关闭留言功能。
除了张文宏,“法律网红”罗翔老师,也在去年清空了微博,主动“退圈”。
在法学领域,罗翔也许算不上大牛,但他通过网络,普及法律知识,更从中探讨人性的善与恶,甚至对一些权力机制提出质疑、作出拷问。
罗翔老师的一些话语,似乎惊世骇俗:
“30天没吃饭快饿死了,见到熊猫吃熊猫,见金丝猴吃金丝猴见到东北虎我吃东北虎,这都叫什么?紧急避险。”
这其实就是对现代刑法的伦理基础——“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以人为本”——的绝佳诠释,闪烁着人性和文明的光辉。
他也对一些热点事件,从法律和伦理的角度,进行酷评:可想而知,有些话难免得罪人。
幽默诙谐的语言风格,融合着深厚的专业素养,和赤子的良知。
罗翔由此走红,但也承受了种种非议。
捕风捉影的曲解、放大,对所谓“不当言论”的扣帽子、打棍子,无中生有的破污、谩骂,都滚滚而来。
罗翔如果有不当言论,网友当然可以批评指正;但批评需要理性客观,就事论事。
但他遭受的,是捕风捉影、恶意中伤,这没有事实和道理,是赤裸裸的群体暴力!
罗翔愤然退出。
这样的网络,这样的“人间”,确实不值得!
而那些热衷于谩骂、举报的人,或曰群氓,则继续留在网上,或许正在寻找下一个被“群殴”的对象……
这是劣币驱逐了良币,更是傻B驱逐了良心!
究竟应该如何参与公共讨论?
针对上述种种,书中在鞭辟入里的同时,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究竟应当如何介入公共事务,参与公共讨论?”
对众多个体的“选择退出”,书中表示理解,但也为之惋惜。
尤其是,那些依然在“大众舆论场”的人,今后应该怎么办,这更是作者关注的。
“平心而论,没有人真心愿意生活在语言的垃圾堆中,渴望坦诚的交流,是人皆有之的渴求,也是理所应当的。”
我们也许无法具备像张文宏医生和罗翔老师那样的专业能力。
但至少,可以从“我本人”做起,不做“垃圾生产者”。
哪怕环境再不堪,也可以独善其身,不加入“群氓”的行列:不参与公众的“造神运动”,也不参与群体暴力,不做落井下石之人。
哪怕“墙倒众人推”,如果我不参与,或许,就少了足以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批评、质疑,当然是一种权利,对任何人,尤其是舆论场的名人,都是可以的。
但这个过程,需要摆事实讲道理,和对事不对人的底线。
尤其是,要承认“我也可能会犯错”,不要把自己视为真理的化身,更不要以个人情绪的好恶,代替客观的是与非。
每多一个这样的“独立个体”,“群氓”就会瓦解一些。
这个人间,也能少一些“不值得”。
但愿这个美好的期待,不要太过遥远……
图片/均源自网络